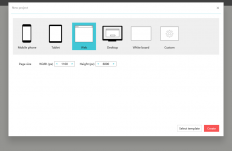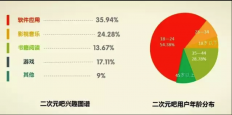那个时候很年轻,朋友的父亲正好又到了创业成功的爆发阶段,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这些多多少少,从商业上,创业上、乃至投资上,综合下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。后来去选硕士专业的时候,我选了一个有商业性质的硕士学位——西北大学的生物科技和商学硕士学位,一半是生化、一半是商业。有很多的医学院,我申请过了,但最后没有选。
在那个时候我才接触到了精英学府,因为之前在马鞍山读的小学、初中,去旧金山的高中,再到大学,都是二流到三流之间。高中我读的是林肯高中,是我们旧金山最烂的高中之一:每天每时打架,墨西哥人打华裔,华人打华裔,越南人打黑人。越南人非常团结,三五个越南人把黑人打得落花流水,所以我们学校经常有警车不停地巡逻。这是一个大炼炉,ABC不喜欢台湾人,台湾人不喜欢香港人,香港人不喜欢上海人,所有人都讨厌除上海外的大陆人。
我们中国人是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端,每天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我又不太会打架,所以要跟人家交流——我跟黑人好朋友,西班牙人好朋友,越南人好朋友,没有人动我;有时候考试帮帮他们,因为我数学比较好,英文一样的差。
那个时间点现在回看,我是在融入不同的人群,跟不同的人交流——善意是互通的,我对这个感触很深。比如我现在骑摩托车,在非洲呆过一个多月;在尼泊尔,在阿根廷、智利,乃至澳大利亚沙漠腹地……我去过很多很危险的地方,这些地方的经历都加深了我少年时代的判断,那便是善意是互通的,你怎么对待别人,别人就怎么对待你。没有无缘无故就要对另一个人施加恶意的人,有的话,数量也是凤毛麟角。
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成长大概都会有七到十个十字路口,在每个十字路口你基本上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如果你做错了选择,走了岔路,你只要能快速地发现,能回来,大概就还能往你想的生活跟工作的方向发展;如果你十个路口连走错三四个,就会越走越偏。
我现在看我五到十个重大的十字路口,大概超过百分之六十是被动选择:
我父母选择去美国,不是我的决策;去西北大学是我的决策;后来我加入投资公司,他们硬逼着我回来北京,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好,又是一个被动的决策。所以到今天为止有经纬这样的平台,我自己觉得是七三之分,百分之七十是狗运,百分之三十是我自己的一些主动选择或者能力。这是实话,就是七三。
进入西北大学最好的部分,是有优质的大公司来校招。因此我进到了投行所罗门兄弟,这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,最后被花旗收购了,所以这个品牌也不存在了。大概二三十年前,他们在行业里是呼风唤雨的,我加入了他们的高科技投行部,在那边做了两年。
正好是互联网泡沫最高的时候,我又去到了荷兰银行,我在荷兰银行待了一年。我记得当时加起来是百万年薪,一个案子没有做。其实这一点都不吃惊,当他们开始做投资的时候,基本上是投资的最高点,他们在最高点进;在最低点,应该投资的时候,他们解散了团队。
那个时候,我记得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,遇到失业。当然他给了我们很好的“遣散费”,但是我就觉得非常沮丧。我是一个对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个了解的一个人。我在一周的时间内,投了四千份简历,全部一样的内容,有时候会改一些,按照他们的数据库发给了投行、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。
所以到今天为止,我还有一个单子:当初我发的陌生邮件谁回复我,这里面如果有任何人现在来找经纬系帮忙就十倍的回报,这发生过几次。大多数公司高管或基金合伙人不回求职邮件的,但也有几个人回复,我深深地记得他们是谁。我就等着,有可能要等上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,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,但只要发生的那一天,我就会用十倍的努力去回报他们。当然我对记仇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逻辑,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我也记得,总有一天碰到他们擦边经纬系边界之时,我会再去收拾他们。后者基本上是不靠谱的投资同行,之前系统性折磨经纬系的创业者,反悔过好几次的,这种人我等着收拾他们。